在朱青的眼里,2020年世界税收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双支柱方案蓝图文件”。
朱青是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长年从事国际税收的研究与教学。他觉得,当今各国经济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传统的国际税收规则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步伐。OECD(经合组织)所领导的有137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包容性框架在应对经济数字化对国际税收规则挑战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应当得到赞许。“但从两个蓝图报告来看,双支柱方案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其前景也不容乐观。我个人对双支柱方案的评价简单地说就三个字:繁、难、悬。”

朱青所说的蓝图报告是2020年10月OECD发布的《数字化带来的税制挑战-支柱一/二(PillarOne/Two)蓝图》报告。这份报告包括支柱一和支柱二两大部分,即上文所述“双支柱”,其中支柱一侧重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征税权分配机制,支柱二则侧重解决剩余利润转移和税基侵蚀问题。该份报告是OECD在20国集团授权下编制的一个有关国际税收规则改革的提案。
一些欧洲国家一度开始先行动作,2019年法国参议院即已通过了数字税收的法案。此后,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等30个国家都纷纷计划征收数字服务税(以下简称“数字税”)。
虽然,欧盟相关国家率先发起了数字税,但是数字经济发达经济体对欧盟数字税的看法并不一致,2020年6月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针对奥地利、巴西、捷克、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和英国等国已经开征或建议开征的数字服务税(Dig-italServiceTax,DST)进行“301条款调查”。这是继2019年7月美国首次对法国数字服务税开展调查之后,进行的第二次有关数字服务税的“301条款调查”,也是调查范围更大的一次,目前该项调查已接近尾声。
据报道,鉴于奥地利、意大利和印度已经完成数字服务税的立法,美国决定近期先对这三个国家进行关税报复。朱青认为,美国的这一做法显然是为了打压各国纷纷开征数字服务税的势头,以此来给这些国家“泼冷水”。
而在国内,由于监管层及专家对数字税的频繁提及也引发了公众的关注。从法国落地到欧洲其他国家纷纷开征,数字税将会是一个新的税种还是在以前税收架构中的加税措施?对于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会有哪些提醒和借鉴意义?
对此,1月19日,经济观察报专访了朱青教授,就数字税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经济观察报:数字税作为这几年来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是否是一个新的税种?包含哪些要素?
朱青:应当说,数字服务税这是一个新税种。数字服务税是对数字服务收入课征的一种税收。法国于2019年7月24日颁布法律,决定从2019年1月1日起开征数字服务税,成为数字服务税最早立法的国家。后来在美国引用“301条款”威胁对法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情况下,法国推迟了数字服务税的开征,并同意等待2021年初OECD拿出各方都接受的“统一方案”。继法国之后,奥地利、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土耳其等国也开征了数字服务税;巴西、捷克、西班牙、英国等国也制定了数字服务税方案,准备适时开征。
尽管都称为数字服务税,但各国的税制略有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应税服务的范围:法国数字服务税的应税服务范围包括数字界面(digitalinterface)服务和互联网广告服务(但不包括发送数字内容的数字界面服务);奥地利仅对线上广告服务征税;印度的征税范围仅包括非居民公司对印度消费者线上商品和服务的销售;意大利包括广告服务和数字界面服务;土耳其包括广告、社交媒体和数字界面服务;英国除了社交媒体和线上购物平台服务外,还计划对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征税。
(二)税率:自法国确定数字服务税税率为3%以后,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将数字服务税的税率定在了3%,而印度和英国数字服务税税率为2%,奥地利数字服务税税率为5%,捷克计划采用7%的数字服务税税率,土耳其数字服务税税率更高达7.5%(总统有权将税率提高到15%)。
(三)征税门槛: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土耳其、捷克和西班牙都规定该税只对每年全球应税服务收入达到7.5亿欧元,并且每年来自本国的应税收入达到规定标准的大公司征收。但上述国家来自本国的年应税收入标准有所不同:法国、奥地利为2500万欧元,意大利为550万欧元,土耳其为2000万里拉,捷克为5000万捷克克朗,西班牙为300万欧元。其他计划开征数字服务税的国家也制定了适用公司的门槛,如英国规定的门槛是全球年销售额超过5亿英镑且至少有2500万英镑来自英国应税收入;巴西规定的门槛为全球年销售额超过30亿雷亚尔且至少有1亿雷亚尔来自本国应税收入。印度的数字服务税由于仅对在线向印度个人销售商品和劳务的非居民公司课征,所以只规定了每年2000万印度卢比来自本国营业收入的门槛。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开征数字税的国家大部分都在欧洲?
朱青:这次围绕数字服务税的冲突主要发生在欧美之间,而欧美围绕数字服务税的冲突实际上来自于双方在经济数字化过程中税收利益的矛盾。欧洲企业在数字化方面大幅度落后于美国。据《福布斯》杂志排名的2019年世界上最大的15个数字化企业中,美国占了9家,中国(含香港地区)占3家,韩国占1家,日本占2家,但没有1家是欧洲企业。
在现有的国际税收规则下,美国等国的数字化企业向欧洲国家用户和消费者提供数字服务,并不能给欧洲国家带来税收利益。不能做到“利益均沾”,欧洲国家当然不会高兴。其实按目前的方案即使开征了数字服务税,法国每年也只能收取三、四亿欧元的税收收入,这跟一万三千多亿欧元的财政收入规模相比微不足道,但这里有一个税收权益的问题。欧洲国家认为,美国公司利用数字技术向欧洲国家的用户和消费者提供了大规模的服务,赚了钱但又不向市场国缴税,这不公平,所以要用数字服务税维权,并挽回一部分损失。
经济观察报:OECD提出的双支柱是基于哪方面的考虑?能否在各国之间协调达成一致?
朱青:2020年10月12日,OECD/G20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BEPS)问题的包容性框架(由137个国家组成)就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的双支柱方案分别发布了蓝图报告,并公开征求公众的意见。
2020年12月16日和17日OECD在网站上公布了250多份反馈意见。这些反馈意见既有来自像微软、亚马逊等大的跨国公司,也有来自像BIAC、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等贸易协会,还有的来自税务咨询机构和学术单位。
包容性框架又在2021年1月14日至15日就双支柱方案召开了一次公众听证会,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包容性框架这次在双支柱问题上如此慎重,主要是因为这两个蓝图报告中的双支柱方案对传统的国际税收规则改动太大,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而包容性框架力图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找出各方的交集,推出一个让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但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支柱一和支柱二的创新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双支柱方案的前景并不会太顺利,尽管各方都有推出双支柱方案的意愿,但在具体细节上各方是否能谈得拢,这是目前问题的关键,我们还要再观察事态的进展。
首先看支柱一。支柱一中的金额A主要是解决数字经济条件下的新征税权问题。对于市场国而言,这种新征税权从无到有,这样势必引发跨国公司居住国和市场国之间税收利益的矛盾和冲突。
因此,这种新征税权设计得是否合理就十分关键。目前支柱一中的金额A主要适用于两类服务,即自动数字服务和面向消费者的业务。自动数字服务是最需要重新分配征税权的领域,目前各方争议较小,但适用范围的大小以及该拿出多少利润分配给市场国,仍存在争议,这就需要各国的政治决策。
但对市场国从面向消费者的业务中是否应得到金额A的问题,目前各方争议较大,它涉及到购买和消费活动是否创造价值的核心问题。另外,根据支柱一的方案,跨国公司即使在市场国有机构、场所,要给市场国分配金额B,但如果符合条件也要分配一部分超额利润(金额A)给市场国。也有的国家建议,如果跨国企业已经根据公平交易原则(ALP)将一部分利润留给了市场国,包括营销和分销利润安全港,这时就应当调整金额A分配给市场国的数量,即一个企业集团如果分配给市场国的利润超过了安全港的收益,那么这个集团就不应再给市场国支付金额A。鉴于金额A要给市场国创立一种全新的征税权,“动静”比较大,所以有的国家提出金额A应当分两步走,即先在自动数字服务领域实施,然后再在面向消费者的服务领域实施。美国甚至建议让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自主地选择是否适用支柱一。
支柱一中的金额B是在市场国设立分销机构(常设机构)的跨国公司要用公式法将一部分利润分给市场国的部分,其目的是使在市场国从事基础营销和分销活动的关联分销商的报酬标准化。原来分销商留在市场国利润率的大小是通过 ALP来确定的,实际上是“一户一率”地谈出来的,现在要“一刀切”,由公式算出来。但包容性框架同时也强调:“在金额B下每个给予补偿基础营销和分销活动的固定回报都应当与按ALP原则确定的结果相近似。”不同常设机构承担的功能风险不同,所处的地区和行业也可能不同,其产品营销、分销的利润率也会有所不同,这时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能被双方都接受的营销、分销利润率就非常困难。包容性框架要求这个利润率“应当在交易净利润率法(TNMM)下基于可比公司基准化分析来取得,按产业分别制定,并要有一个适当的范围”,这跟目前 ALP原则下转让定价的方法基本相似。可以说,金额B有“多此一举”之嫌。
支柱二其实跟数字经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实际上是包容性框架搭支柱一的车,出台一个防范BEPS(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全球最低税率机制,即通过确保跨国企业的有效税率不低于一个人为设定的“最低税率”来系统性、综合性地解决税基侵蚀问题。
该方案的适用范围并不局限于高度数字化的企业,具体包括“四个规则”:所得纳入规则(IIR)、低税支付规则(UTPR)、应税规则(STTR)、转换规则。所得纳入规则和低税支付规则合称为“全球防止税基侵蚀规则”(GloBE规则),其中所得纳入规则优先于低税支付规则。应税规则独立适用且优先于GloBE规则,它建立在税收协定基础之上。应税规则适用以后,GloBE规则有可能不再适用,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支柱二最大的问题是各国能否对“最低有效税率”达成共识。一是如何计算这个有效税率。为了顺利推出支柱二,包容性框架还提出了“公式化实质性排除”(formulaicsubstancecarve-out)的方法,即在计算应付补充税(top-uptax)时可以通过公式剔除一部分利润,旨在剔除不易受到BEPS风险影响的实质性活动所产生的固定收益。但哪些利润需要剔除目前各方认识还不能统一。二是最低有效税率定多高?很多发展中国家通过税收优惠鼓励外资进入,造成本国实际税负较低,但这与BEPS性质不同。所以,最低有效税率如果定得较高,就会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税收主权。三是税率是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涉及各国的税收主权,协调起来难度很大。
经济观察报:同样,中国也有比较大的互联网企业,也有比较大的平台消费类企业,数字税的开征对于中国企业的影响在哪里?从现有的结构来看,开征数字税的基本都是数字经济欠发达经济体,中国拥有庞大的数字经济产业,中国未来是否会开征数字税?
朱青:在数字经济领域,我国既有大量的互联网企业作为“卖者”,也有大量的“买者”通过平台消费类企业购买外国的商品和服务,所以数字服务税对于我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通过开征数字服务税,我国也能够取得一部分税收利益;另一方面,如果外国政府对我国企业征收了数字服务税,这部分税款要么由我国的企业负担,要么转嫁给我国的消费者或用户负担。从我国互联网化企业的角度看,它们向世界各国的用户或消费者提供服务,需要税收的确定性,如果各国的数字服务税五花八门,一国一个税率,一国一种征收办法,这时税收的确定性就无从谈起。从这个角度说,我国的互联网企业也都希望国际社会能拿出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不要让各国通过数字服务税“各自为战”。当然,如果国际社会拿不出一个被各国都接受的统一方案,那么我国为了维护国家的税收利益,今后恐怕也得开征数字服务税。


 李真顺
李真顺 贺克斌
贺克斌 梅生伟
梅生伟 周远祥
周远祥 赵华林
赵华林 曾毓群
曾毓群 朱共山
朱共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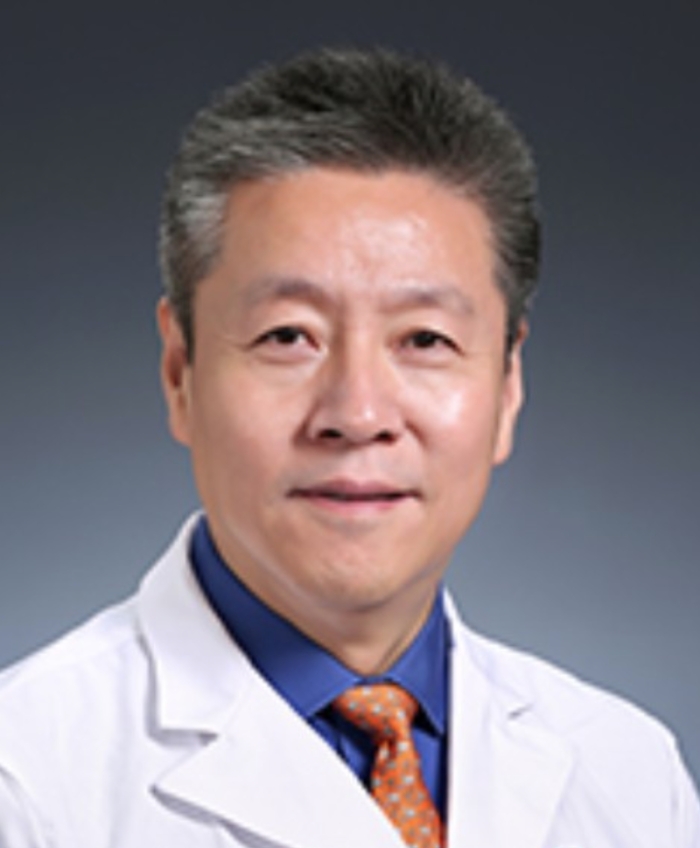 王国玮
王国玮 毛宗强
毛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