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实现过程中,需要把握快变量节奏,重视慢变量速度,防止转型节奏失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李继峰
“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存在快变量和慢变量,如果两类变量之间不能够匹配,就会带来转型的风险。”在9月22日《财经》杂志主办的“第二届碳中和高峰论坛暨中国上市公司碳排放排行榜发布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李继峰在演讲中表示。
此次论坛中,李继峰分享了对中国减排路径及绿色低碳转型风险的思考。
李继峰认为,绿色低碳转型不同于历史上两次能源转型。煤炭替代薪柴,油气取代煤炭,前者并未完全消灭后者的需求,在开始转型后的较长时期内,后者的需求仍然有所增长,属于增量转型。而碳中和目标下的未来能源低碳转型却是替代式转型,要用清洁能源高比例替代化石能源。
在这样一场替代式转型中,存在快、慢两种变量。快变量包括政府以超前的减排雄心试图占据引领地位、金融资本助推提高预期等。而慢变量则包括存量资产处置、技术攻关,及商业模式和消费者理念转换的迟缓。
快慢变量的节奏失衡可能会引发转型风险,比如去年欧洲碳价过快上升就体现了这一点。李继峰认为,推动绿色低碳转型需要把握好快变量的节奏,既要适度压力,又要避免过度超前,同时,由于慢变量演进速度决定了整体转型节奏,因此需要超前布置基础设施、重视技术创新、凝聚社会共识。另外,除了潜在的节奏失稳风险,转型还存在叠加的极端天气风险,以及衍生的信息安全风险。
针对中国自身的减排路径,李继峰指出,中国实现碳中和必须要统筹发展、减排和安全,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长期的关系。从发展的需求看,如果到2035年实现人均GDP翻一番,那么15年的GDP增速大概要在4.7%左右,在这样一个仍需较快发展的阶段实现碳达峰,是此前发达国家没有实现的。在此过程中,还要保障能源安全,这对中国来说挑战巨大。
他还提到,自改革开放以来的8个五年计划中(1980年~2020年),有6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碳强度的平均降幅在4%左右。但是在未来的8个五年计划中,碳强度年均降幅要达到8%~10%。而实现这样的碳强度降幅跃升,不能只依靠过去熟悉的节能减排工作,必须要在此基础上,寻找更新的东西来支撑,包括新的制度、技术、理念、产业结构、商业模式等等。
尽管减排压力日益增大,但能力提升却不会一蹴而就,中国的碳中和“拖不得”也“急不得”,必须科学合理设定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路径。
李继峰认为,源头减排仍然是实现碳中和的主要方向,要稳步推进能源利用碳排放下降。长远来看,则需重视工业化碳吸收技术对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兜底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加强非二氧化碳气体排放管控。
具体到碳中和的实现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需适时调整减排着力点:达峰阶段(2020年~2030年),重点在于强化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改进;转换阶段(2030年~2035年),推动节能与能源结构优化并重;深度减排阶段(2035年~2050年),需要多措并举;攻坚阶段(2050年~2060年),则可以利用CCUS技术兜底。其中,李继峰特别强调了转换阶段。他认为,在实现碳强度降幅跃升的过程中,大概需要5年时间对减排制度、政策、技术等进行压力测试。
李继峰还列出了几个影响未来碳中和路径实现的关键变量,包括新建建筑面积规模变化、老旧汽车淘汰速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进展,以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势头。
提及中国的绿色转型发展策略,除了前文所述的平衡好快慢变量,李继峰还提出,另一个重要策略是利用好数字化与低碳化的融合。“替代式转型的过程是痛苦的,我们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数字化刚好能实现这一点,它能够放大经济效益。”李继峰说。
以下为李继峰演讲全文整理:
大家好,非常荣幸第二次受邀参加《财经》杂志碳中和论坛。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中国碳中和趋势的个人思考,如果有不一定正确的地方,请大家见谅。
刚才中创碳投的唐人虎总经理用几个数字来讲碳中和,他提到了2、3、4、5等,我觉得缺了一个“1”。这个“1”就是“1+N”政策体系的“1”,也就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我们未来所有实现碳中和的工作,都要按照这样一个总体的思想来实施。
这份文件的内容大家都很熟悉了,里边包括了三个方面的总括的内容,包括目标、要求、路线,还有七个方面具体行业的指引,最后还有三项的保障措施。所以我觉得整个来看,我们实现碳中和要围绕着这个“1”来做,这是我们的一个纲领。
对这个“1”的认识,我觉得核心在于,中国实现碳中和必须要统筹发展、减排和安全。我们要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当然,这个事情确实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到2035年需要实现人均GDP比2020年翻一番,这意味着我们15年GDP的增速大概要在4.7左右。如果我们假设到2060年比2035年再翻一番,可能我们的GDP(增速)要到2.8左右,这实际上和发达国家GDP增速是差不多的。但2035年之前的增速,意味着我们要处在一个较快的发展阶段,而要在这个阶段实现碳达峰,是之前发达国家也没有出现的,对我们来说挑战还是不言而喻。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同步实现3060的目标,还要满足能源安全的要求。刚才大家已经提到了能源安全问题,尤其是在今年,爆发了一系列地缘政治的事件等,使得安全问题特别突出。我们的能源未来总量上还要增长20%左右,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要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巨大的转型,我后面也会具体讲讲转型的风险。
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安全问题实际上比我们以前认识的可能要难得多,所以在碳中和的过程中,安全问题也是需要高度的重视。
基于这样的一些认识,基于“1”的统领,以及刚才提到的,要统筹考虑三个方面,我今天想给大家贡献两个方面的思考。
第一个,关于减排路径的一些基本认识。一直以来,有很多机构在研究减排路径,特别是最近几年,很多国内外的机构都发表了关于中国碳达峰碳中和实现路径的思考,各家机构的情景假设都不太一样。总体来看,可以分成保守派和激进派,或者可以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但无论如何,都是以推动中国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为最终目标。
当我们在考虑中国要怎么走的时候,做政策制定的时候,都会基于这些研究,提炼出一些共识的东西。比如对于转型的认识,对于CCUS这种封存技术的认识、它的角色定位等等。基于这样的一些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规划未来的路径。
在这之前,我们需要意识到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在未来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过程当中,跟过去相比,跟1980年到2020年这8个五年相比,我们碳强度的降幅是要明显提升的。过去的8个五年计划,有6个五年计划期间,碳强度的平均降幅都是在4%左右,但是未来的8个五年,可能碳强度平均降幅要达到8%~10%。
怎么理解这个数字呢?这可能意味着,我们在过去的道路基础上,必须要有更新的东西来支撑,需要有新的制度、新的技术,新的理念、新的产业等等。
这些不是以当前时点为基准,而按照过去的路径发展,在这个基准的路径上再找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过去推行很多制造业重点行业的节能减排,未来这些工作还要继续做,但这些可能不是我们讲的新,而是要在这个基础上找更新的东西,包括新的思路,各个方面的创新等等,来实现我们碳强度降幅的跃升,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围绕着这个概念,我们提出要科学合理地设定战略路径。首先就是要保证两个目标时点的达成,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我们所有工作的目标导向。达成的过程,还有个节奏的问题,也就要与我们减排能力提升的节奏基本同步。这个工作不能拖,但是又不能急,尤其是目前这个状态下,因为你的能力提升要有个过程。
这里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源头减排是主要的方向。有些研究讲我们现在可以继续排,到时候基于CCUS,或者一些减碳、碳汇技术的大幅度增加,是不是可以直接解决?但从整个数量的对比来看,我们现在每年排放100多亿吨的二氧化碳,森林碳汇能力大概在10亿吨的水平,是100比10的概念。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此消彼涨,但是整体上来看,减排还是我们整个实现碳中和最核心的或者是主要的方向。
刚才讲源头减排是我们的主要方向,但是到了2050和2060的时候,可能源头减排的潜力基本上就没有了。如果需要确保目标实现,我们要有CCUS,也就是工业碳吸收的方式来兜底,这个作用也是很突出的。关于二氧化碳的利用,还有一些未来的方向,比如说我们在化工上面是不是可以把二氧化碳作为一种新的化工原料,用这种方式来实现碳中和。这些对我们未来实现碳中和是十分重要的技术,虽然目前看来这个技术还比较远,但是我们要开始它的研发和储备。
最后就是我们非二氧化碳气体的管控。
我们把实现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里边,首先从减排这个角度来看,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重点。
比如说我们在达峰阶段,重点还是要通过传统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改进,因为这是现在我们很熟悉的手段和方式,也是我们正在推的,在达峰的时候,它还是发挥主要的作用。
之后还要有一个转换的阶段,从减排上来看,我们要实现节能和能源结构的优化并重。大概在2035年,非化石能源的比重会超过煤炭。2035年前后,对于整个能源结构来说,是一个结构性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我们提出来结构和节能并重。
再之后要多措并举,深度减排,我们要实现每年碳强度降幅能够达到8%-10%的水平,这时候要多措并举,能用的都要用得上。
最后要有一个攻坚阶段,要有一个技术兜底。
另外,减排的节奏要与我们的能力相匹配,比如技术储备、体制机制的改革,我们为什么设置了一个2030-2035的转换阶段呢?就是说达峰阶段的时候,碳强度的降幅可能和我们过去几个5年时间差别不太大,可能略有提高,但到了深度减排的时候,我们要实现碳强度很高的降幅。这两个阶段的转换过程,我觉得实际上是需要压力测试的,我们这些政策、技术能不能从一个比较快到很快阶段的转换,实际上我们需要有一个5年的时间去做转换。
这其中,我列出了一些关键影响变量,比如在整个减排过程中新建的建筑面积。如果继续按照目前房地产的建设进度,可能会导致多排放50亿吨左右的二氧化碳;比如老旧汽车的淘汰,能不能把更多的汽车销售空间让出来给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等;比如制造业运营效率的提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对很多人来说,制造业节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再比如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其实技术或产业现在大家都比较乐观,但体制和机制还存在一些障碍,这块也需要尽快补齐。这几个关键变量会影响到我们未来路径的实现。
最后,我想对转型的风险做一点点思考。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绿色转型跟历史上两次大的能源转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历史上两次大的转型,一个是煤炭替代薪柴转型,一个是电力和内燃机推动的油气发展的转型,这两个转型从技术发明到实现规模化都属于增量转型,当我们大规模使用煤炭的时候,薪柴并没有完全被替代,而且还有一点小幅增长。当我们油气大幅增长的时候,煤炭也并不是没有增长,这些都属于增量替代。
而到未来2050年的能源低碳转型时,我们是100%的要去替代非化石能源,从一个增量转型完成变成了一个替代式的转型,这时候我们的转型压力跟过去相比远远要提高。
这个转型过程里实际上有快变量、有慢变量,我们现在讲转型的节奏,节奏里有快的也有慢的,比如现在目标的提出,可能大家就容易就提一些彰显减碳的目标,越提越超前、越提越快。
如果从博弈论来看,在一个趋势明确的情况下,领先者是有这种占优策略的,我提一个更强的目标,把我的优势提出来,落后的国家也会有跟随减排的要求,那么目标就会越提越快。
还有一个快的变量是我们的金融资本,资本可能跑的比企业还要快,也会超前,这些是快变量。慢变量就是我们存量资产的处置,包括我们技术的攻关,以及商业模式、消费者理念的转换,这些变量可能不会那么快,以及配套政策能不能匹配,如果两个快变量和慢变量之间不能够匹配,就会带来转型的风险。从去年欧洲来看,碳价过快上升实际上就体现了这一点。
从我们中国来看,绿色转型有一些重要策略,比如要用好数字化和低碳化的融合,它是一个替代式的转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非常痛苦的,我们就要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数字化刚好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它是能够放大经济效益的。
我理解在我们低碳化转型过程中,不可能离开数字化的转型,必须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才能够更顺畅地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另外,我们要控制好节奏,把慢变量的演进速度作为我们的一些转型节奏的控制,因为慢变量的演进速度决定了整体转型的节奏。我想强调一点,虽然我们过去在产业技术进步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如果我们从单位增长值能耗角度来看,很多产业的效果在过去几年还是不够理想的,未来还是需要有更大的实现增加值碳强度下降的政策。
最后,总结一下我们转型面临的三类风险:潜在的节奏失稳风险、叠加的极端天气的风险、以及衍生出来的信息安全风险。这三类风险未来可能都是我们实现碳中和路径上必须要考虑的风险。


 李真顺
李真顺 贺克斌
贺克斌 梅生伟
梅生伟 周远祥
周远祥 赵华林
赵华林 曾毓群
曾毓群 朱共山
朱共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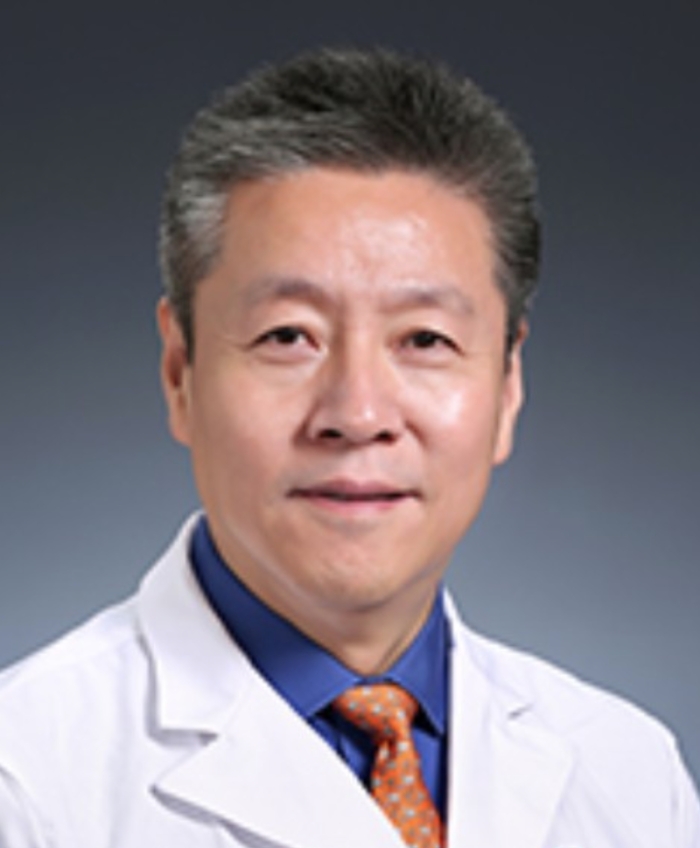 王国玮
王国玮 毛宗强
毛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