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研究的“照着讲”与“接着讲”
文 | 宋洪兵
新世纪以来,法家研究呈现了一些显著变化,亟待我们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和回顾,同时去展望未来的法家研究,所以关注“法家研究往何处去”这样的话题,是非常有意义的。刚才听各位老师的发言,对我来说,收获很多,也让我非常振奋。
蒋老师谈的综合创新方法以及在人类文明、社会结构、历史化的视野中研究法家,可以说是高屋建瓴。蒋老师事实上提醒我们把之前接受的各种观念先给它悬置起来,然后深入到思想理论的底层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底层,从理论底层去思考最为原始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基础性,所以启发非常大。武老师的“大法家”观念,还有强调法家思想史应该放在中国文化的历史语境之中去理解,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很大启发,正如喻中老师说的,我们的法家研究要往宽了去。韩老师讲制度与伦理不一致的问题,说中国历史上法家制度与儒家伦理是两层皮,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思考。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我们是否还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也值得我们思考。
任老师提出的很多观点我都非常认同,尤其是政治与思想的关系问题,政治家肯定是一种实用主义,拿来主义,他不会按照思想家所想象的那样去用,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并且,“偏不足为诸子讳”,整个诸子思想都是一偏,所以不可能指望法家研究去为中国未来的出路指明方向,我觉得这对于当代法家研究是一个不可实现的幻想。事实上,法家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上升到非常现实的层次去思考问题。但是这背后有没有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或者我们走到今天是否还蕴含历史层面的东西在里边?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刚才听任老师讲中国古今的结构之变,我们会看到一种古今断裂。任老师提倡区分法家研究的思想史与思想两个维度。我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思想史的研究本身是要为了呈现思想,所以思想史与思想是不是能够把它割裂开来?如果在思想史研究之中,我们研究出来的思想根本就不具备一种智慧启迪的话,那这种思想只能是一种死了的思想,刚才各位老师都提到了,说不要把法家说死了。法家在某一个时代会有一个时代的呈现,但是它背后的那种思想原则,那种思考政治问题的方式,可能依然在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古今断裂确实存在,古今延续,是否也存在,这些问题,是任老师的发言给我的启发。
我今天大致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法家研究如何“照着讲”
第一个问题,就是法家研究“照着讲”的问题,这大约对应着任老师说的“思想史”的维度。我觉得我们在未来要做法家研究,要做一种尊重文本的正本清源式的研究。古今法家研究,各种成见和偏见太多,充斥着研究者太多的情绪化立场,古代儒生的暴政批判和现代学者的专制批判,基本就把法家学说给完全否定了,没有做到全面理解,更别提“了解之同情”。这些年我一直在提倡全面理解法家。比如,法家思想有道德观念吗?如果尊重法家文本的话,法家为什么不能有道德?或者是法家的道德观念与他的政治思想之间是不是可以并存?如果说法家没有道德,又是从哪一种视角来切入?有确凿的证据吗?如果从文本的角度来去理解法家文献,法家思想就有道德的因素。所以我主张法家研究应该做到“内部解读”,反对先入为主的“外部解读”,应该在法家文献的正反证据中寻求对法家思想的合理理解,不要只看到对自己观点有利的证据,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对自己观点不利的反面证据。这样,我们才能够最大限度地相对公允地去研究法家。中国历史上法家研究的整体情况,要么是儒家的仁政或德治立场,要么就是现代西方的民主自由立场,完全把法家完全置于一种对立面,这样为了凸显某种价值而将法家视为一种被审判的“他者”,很难真正理解法家思想。
正本清源式的法家研究,有三个层次:第一,解决“是什么”的问题,涉及法家文献的全面理解;第二,解决“为什么”的问题,涉及法家思想源流及历史背景、思想家的个人偏好等;第三,解决“怎么样”的问题,对法家思想进行判断,尤其需要研究者对自身立场和价值的反思和自觉,这个层次最难,很多争论都是立场之争。并且,很多立场之争,又与第一个层次的全面理解纠缠在一起,导致法家研究的沦为某种价值立场的宣泄。法家研究之所以不能得到相对客观地研究,根本原因就在于第三个层次的价值立场和前提预设层面,很多研究者在具体开展法家研究之前,观念中就已经具有了一个定见。如此,势必影响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的文献选择和文献解读。如果说我们在“是什么”的问题上都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那么在“为什么”和“怎么样”的层次上又往往会出现偏差。由此,造成一种恶性循环的法家研究现象。要全面理解法家,先不要着急去对它进行价值判断,应该立足于“是什么”的基础之上去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
二、法家学理“接着讲”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法家研究“接着讲”的问题,这大约对应着任老师所说的“思想”的维度。我在从事法家研究的过程之中,总是有意识地留意我所研究的对象中是不是蕴涵着某种普遍性的思想,也就是法家思想的学理是否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萧公权曾说,法家学理从秦汉时期就终止了发展,帝制时代的思想家们,几乎没有谁在先秦法家学理的基础上“接着讲”法家,这跟儒家在中国历史上不断推陈出新、不断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法家学理本来应该具有一种开放性,蕴含着多元性和可能性,汉代儒生一下子把法家说死了之后,后边没有人愿意去把法家的学理往下“接着讲”,使得人们提起法家自然而然地想起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法家。但是即便是如此,在中国历史上依然会存在着一些实践法家的现象,我将其概括为中国历史的“法家议题”,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思考。
从法家学理来看,法家哪些观念具有普遍性?或者法家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如果说法家学理只存在于先秦时期,那么从汉代以降一直到清末乃至今日,“法家议题”是否还持续影响着历史与现实?正如韩东育老师所说,法家在中国历史上被骂了两千年,同时又被用了两千年。出现这种现象,难道只是邪恶因素在起作用吗?是否蕴涵法家说对了人类政治生活之中的某些不可改变的原则的意味?法家的政治思维方式是否依然还存在于我们的观念?这涉及到如何提炼法家学说的学理以及如何对待中国历史上的“法家议题”两个方面的话题。
法家的学理,蕴涵着一种普适性原理。法家学理首先体现为法家的历史哲学。法家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强调对人类政治认清所处历史阶段的时代主题并做出有效回应。法家历史哲学实为政治哲学的根基之一。任何政治家,都必须认清时代潮流并提出有效的应对方案。政治有务虚的层面,但是政治本质上必须要务实,必须要解决实际问题。
其次,法家的政治正当性理论具有普适性。法家基于时代主题之准确判断并做出有效政策调整,最终有利于天下百姓并由此获得统治正当性的观念。政治正当性的问题,西方政治哲学讨论得很深入,法家有关政治正当性的说法,卑之无甚高论,但却说中了政治获得百姓认可的最为坚实的基础,那就是政治能否给百姓带去切实的利益。所以,法家不是没有道德,法家会认为,无论哪个时代哪种制度,能不能给百姓带去利益,从而让百姓受益,这是最为关键的。光说不练,或者只开空头支票,或者只看某种形式,忽略民生效果,如何能够获得正当性?
第三,法家的内治外强观念具有普适性。内治,就是内政治理,外强,就是对外具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基础。法家认为,内治离不开法治,离不开一套客观运作的官僚制体系,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那套官僚制。法家在“大争之世”讲内治外强,但内治外强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很重要的东西。当然,内治会因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是法家强调的“规则之治”并非简单的rule by law,而是与官僚制联系紧密的一套治国理念。严复其实也特别强调内治外强,这既是一种军事实力,更是一种综合国力,对一个国家的自我保存至关重要。
第四,法家看待政治的思维方式具有普适性,这是法家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法家发现了人类政治的本体或人类政治的本质,在于以支配—服从为基础的权力博弈,认为统治者不仅要有能力做出实际业绩,而且还要有能力灵活应对内外权力挑战巩固自己的统治,法、术、势不可或缺。法家一方面讲法治,所以强调“法”;另一方面讲政治的权力斗争与博弈,所以强调“术”与“势”。法家讲法治的时候,君主也需守法。但是法家很清楚,只讲法治,君主无法真正治理好国家,阴谋权术、权力斗争、利益纷争,哪一个时代、哪一种制度、哪一种文明不存在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政治与法治属于两个领域。我认为法家发现了人类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你说是困境也好,你说是根本处境也好,就是政治有黑的一面,就是权术的一面,有权力压制的一面,同时也有白的一面,公正的一面或者正义的一面。法家的这种思维方式,我觉得是一种贡献,体现了法家的“理论真诚”。法家学说的根本特质,在于他们面对人类政治或者面对人类真实的生活情况的时候,说实话、办实事。
总体来说,法家务虚的东西少,务实的东西多,所以政治家不能把法家说的这些真实情况跟百姓讲,毕竟政治还是要务虚的。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具有天然的优势,适合“缘饰”政治,适合务虚。古代中国形成“儒法国家”,其实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必然逻辑。所以,单纯依靠法家学说不足以建构一个好的社会,但是违背法家的上述学理的国家,不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理。法家的学理,是建设一个好社会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三、中国历史上的“法家议题”
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法家议题”。法家作为一个思想流派,从汉代开始就基本隐退。但是,隐退并不意味消失,因为它依然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简单讲,法家的治强观念,内在地规定了中国自秦以降的中国政治的思维方式与实践模式。治强,都属于广义的政治,涉及到内政治理及综合国力问题。对此,法家虽然自汉代以降被斥为“治道之贼”,但因其理论地位及思维方式之于政治问题之不可或缺性,故而出现了“阳儒阴法”“外儒内法”或“儒法并用”的政治模式。人们可以骂法家,但是法家却始终存在,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文化奇观。原因何在?我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法家对人类政治的深刻洞察以及他们的政治思维方式,说到了人类政治的痛痒之处,人们可以不喜欢,但无人能够否认其洞见。历代政治家及历代政治实践,正是在此意义上离不开法家,虽然意识形态层面总是以儒家思想为主。
首先,“法家议题”之一,就是人的德性与法的规则,哪种更重要的问题。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儒家的观念主导了帝制中国的法治实践,于是便有了瞿同祖先生的“法律儒家化”的说法。现在,这种观点日益受到挑战,“法律法家化”的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比如,从事中国法史研究的武树臣先生、杨一凡先生等,最近都从古代法治实践的角度去分析法家因素的影响。
其次,“法家议题”之二,就是法家有关人类政治的深刻思考,使得帝制中国每一时代的统治者都不得不认真对待。明代学者周孔教说:“自三代以降,操其术者十九。”君主要治国,就不得不思考如何应对纷繁芜杂、勾心斗角的权力斗争。参与国家治理的实践者,不得不思考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如何才能维持自己的政权,如何内治外强,如何应对各种现实挑战。在此方面,法家提出了诸多无可替代的方案。对于绝大多数统治者来说,法家对人类政治的深入阐述,是他们的必修课,必然经历的“政治启蒙”。
再次,“法家议题”之三,就是如何富强的问题。战国时期的法家,主张以“农战”富强,利出一孔。但是,自汉代以降,“农战”话语隐退,如何充实府库的官营思路凸显,由此形成是否“与民争利”的长期思想论争。“盐铁会议”御史大夫与贤良文学的争论,王安石变法以及张居正变法时期的争论,都是围绕此一“法家议题”而展开。每当进入衰世或外敌威胁的时候,法家思维总是不断出现在中国历史,挥之不去。直到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面临瓜分豆剥的困境,三千未有之大变局来临,法家同样出现,并伴随着西方的进化论,从幕后走向前台,以“国家主义”的身份参与现实问题之讨论。20世纪30年代,“新战国时代论”更是横空出世,提倡以“新法家”应对民族国家时代的“大争之世”,治强观念在此发挥重要功能。
最后,“法家议题”之四,就是法家塑造了一个“强国家”传统。“强国家”传统涉及国家治理的一个根本问题:由一个强大的国家治理好,还是由多数分散的权力组织来治理好?中国历史走出来的道路,就是形成了一个“强国家”传统。福山认为,先秦法家学说缔造了一个“强国家”传统,国家能力很强,赵鼎新也说帝制中国是一个“儒法国家”,相对于其他文明传统,中华文明自秦汉以降的政治实践中,以皇权为核心的国家权力始终未能受到社会力量如宗教力量、贵族力量等的制约,甚至像样的权力博弈都很少见。法家缔造的强国家传统,是一个中性遗产。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维护了中华文明数千年而不衰,没有像西方帝国那样四分五裂;消极的一面在于公权力没有得到切实制约,人民权利难以得到保障。
强国家摆在面前,该怎么办?很多学者认为源自西方的现代“法治”(rule of law)是一种可行之道。但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包括今天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基本都是从各种力量之中博弈出来的,不是从大脑中想出来的,实现“法治”要有社会力量来维护法治之落实。西方的rule of law,背后有一个维护法的社会力量,如果没有维护法的力量,如何rule of law?这是一个问题。
在“强国家”传统中,法家的“法治”常常被视为rule by law,以此区别于现代西方的rule of law。像任老师刚才提到的rule by law和rule of law的问题,提到的个人权利保障以及公权力的约束这样的现代“法治”问题,其实也面临着一个困境。任老师的“法治”(rule of law)其实也面临着一个法家式的困境,就是说先秦法家想实行“法治”的时候,他们感到力不从心,当代要落实完全的“法治”可能吗?任老师提出来的标准或许也面临困境,就是说真正的法治可能吗?这可能是人类的一个终极的困境,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去解决西方构建的那样一个“法治”理想,即使对西方文明来说,也是理想,他们也没有真正能够实现。我这么说并不等于说他们的“法治”在实践层面跟非西方国家一样,他们有做得比较成功的地方,很多值得我们借鉴。但从根本上讲,“法治”(rule of law)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这跟人类政治的本质有关。人类政治离不开权力斗争与利益纷争,也离不开政治人物的智慧和勇气等能动性的因素,很多东西很难用一种公共普遍的规则去约束。归根到底,政治与法治,其实是两个既交叉又各自独立的两个领域。以法治去覆盖政治,更多体现为人类的一种观念形态,至今没有看到真正的实践形态。因此,当以一种当代人依然感到困难的“法治”(rule of law)去苛责法家的“法治”只是君主治国的工具所谓rule by law时,我们想过没有,法家文献里何曾主张过君主不必守法的观念?法家的法治理想里面,是不是也蕴涵着rule of law成分?只不过法家比现代人更真实,他们还意识到“法治”并不能真正替代“政治”。
“强国家”传统还涉及一个如何与社会达成和解的问题。秦朝统治有很强的法家色彩,奠定了“强国家”传统的基调。但它没能达成社会和解,所以二世而亡。汉武帝 “罢黜百家,表彰六经”,重用儒生。通常认为,重用儒生是因为儒家观念对于政治治理优于法家。现在看来,古代帝王重用儒生,并非看重儒生的才能,而是借重儒生对于社会底层家族、宗族的影响力,实现了一种国家与社会的政治和解,从而维持了社会的稳定。这是赵鼎新的一个敏锐发现。这种政治和解带来的代价就是把儒生(列文森所说的国家治理的“业余爱好者”)带到了官僚制里边,它会导致一个既败坏道德又污染政治这样的一个负面效果,但这个负面效果有一个很大的成绩,就是就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和解。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当儒学在1905年脱离了科举制成为“游魂”之后,国家与社会如何达成和解?那么儒家思想的家族观念,日益萎缩,同时又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贵族阶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和解是如何实现的?我觉得我们在思考法家议题的时候,应该认真对待。很多人会说“皇权不下县”,然后就国家权力一竿子插到底,是个体面对强大的国家等问题,但这背后的问题可能很复杂,并非如此简单,值得深入研究。
法家如何应对当今的各种现实问题,能否从法家学理层面提出应对“当今”问题的法家方案,这也是未来法家研究应该着力思考的重点。当今中国发展的脉络,依然在传统中国的延长线上,中国复兴深刻表明当今中国与传统中国的内在关联。当今中国的复兴,法家思维,是否可以成为一种视角?很多西方学者或国内自由主义者看不懂或不理解的中国复兴的逻辑。西方现代政治基本以个体作为原点,然后来“重构”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由此形成西方的契约论传统。中国复兴的逻辑,其实就是“强国家”传统之下的治强逻辑。在此逻辑之下,国家与个体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而非任何一方压制另一方的问题。执政者必须要给百姓带去利益,同时要根据时代特征考虑百姓的忍受程度,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动态平衡。就此而论,中国传统思想或许还在起着作用,虽然我们有结构之变,但从长时段来看,是否也意味着一种古今延续?


 李真顺
李真顺 贺克斌
贺克斌 梅生伟
梅生伟 周远祥
周远祥 赵华林
赵华林 曾毓群
曾毓群 朱共山
朱共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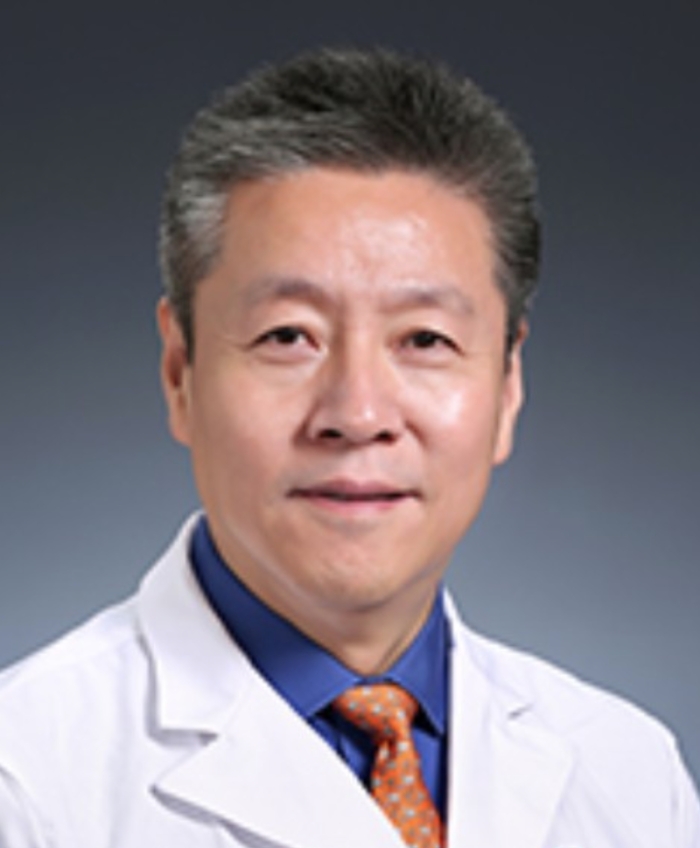 王国玮
王国玮 毛宗强
毛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