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本质:精英教育或是普及教育?
周忠和:各位晚上好,今天我们围绕“大学有什么用”这个主题进行讨论。首先,请各位老师从历史的视角谈谈在大学的演变过程中,其内涵发生了哪些变化?大学的本质是什么?
如果说还有第七个关键点,我认为是2020年。中美关系、新冠疫情、整个经济发展出现挫折,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2020年以后的大学该往哪个地方走、会面临什么困境。在调整过程中,经济、政治和教育三者之间的互动,是我们必须讨论的话题。
周忠和:从您上述谈话中,得知大学经历过六个关键时期的发展,甚至马上迎来第七次的变革,这些变革受到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形势的影响非常大。在这种背景下,关于大学的本质和使命的探讨至关重要。李老师,请您讲讲看,您心目中的大学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一直不变的部分又是什么?
我们的大学从精英教育阶段过渡到大众化教育阶段,再到今天的普及教育阶段,用了不到20年时间。
周忠和:欧美国家大学使命的变化经历了多长时间?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人文学科正在走向衰退吗?
陈平原:我的担心是就业形势琢磨不透,今天的热门专业,毕业后可能找不到工作。有一段时间,学文学的就业很困难,都提倡学金融。后来做统计,最难就业的却是国际金融,因为办的太多了。所以靠热门专业来推动就业或者吸引学生是很危险的。反而,我觉得长线的专业更值得关注。今天大学过分地强调适应市场需要来设置专业,导致学生们选择专业时很茫然。
周忠和:总体上,我感觉大学受到市场务实风气的影响。在这种有用的评价体系下,人文学科有没有前途?学生还要不要学无用的知识?这又回到了大学的本质问题。
曾湘泉:专业设置不能太窄。英美讲究通才教育,这也涉及到就业问题。专业设置首先要研究需求分析。像工程类的专业,尤其需要和市场结合。而人文学科不应该按照这个方法来进行评价,它的特点是适应度比较广,无法一对一快速培训。
陈平原:在大量扩招过程中,很多地方需要迅速地完成任务。相比于工科,文科的投入相对比较少,所以扩大比较快。但我觉得市场经济会调节,例如在广东,什么专业的学生出来找工作有困难,就减少或关闭。日本的国立大学也在这么做,连续几年每年减少,理由就是国立大学拿的是国家的税钱,要提供有用的学科。
周忠和:李老师,你认为人文学科的前景会不会受到实用主义的思潮的影响?
李志民:我还是强调我的观点。第一,上大学不等于就业,把大学和就业挂钩本身还是在生存层面上思考问题。第二,学什么专业就能找到什么工作,这个也不是严格对应的。大学是知识层次的提高、能力的提升、思维的训练,这是人的整个生命层次的提高。从这个角度看,人文学科很重要。还有一个层次可以思考,今天的本科不是最终学历,学生可以在大学期间发现自己在哪方面有特长或兴趣,考研的时候可以继续深造。
周忠和:我们注意到很多大学生有就业焦虑,如何破除这种焦虑?从学生和从学校的角度来说,我们怎么样适应当前的这样一种形势呢?
陈平原:北大会给大一的新生配备导师,我们系里所有的老师都必须负责一个学生。因为学生从中学刚转到大学的时候,会没办法适应新的大学生活。考进北大后,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因此学院很关注这些学生的情况。
但大学还是有很大变化,以前大学四年是很愉快、充满生机活力的。现在学校的这套考试制度给学生带来了很多压力。10年前,北大中文系大概80%的人能上研究生,现在降到50%以下。很多单位只招硕士生及以上,所以很多人不得不继续深造。这样大学就变得和中学一样了,问题出在这个地方。
李志民:我不知道像北大这样学生拼命竞争、追逐绩点、争取保送的学校有多少。前两年我一直主张的是我们的大学要针对打游戏、躺平这些事情,从管理上采取一些措施。
比如应该从学位分级上调动学生内生的动力。全世界多数的国家是大学宽进可以,严出的问题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宽进实现了,严出也还没解决好。但英国采取了一个好的方法,它把学位分成荣誉一等、荣誉二等、荣誉二等的甲乙丙丁几类。荣誉一等和荣誉二等甲类的学生,教授就可以直接推荐他们上研究生,就不用考了。
关于未来,我们需要更包容
周忠和:我们畅想一下未来的大学。人工智能技术革命兴起、人口结构的改变,给大学的教育和就业规划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陈平原:如果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人类,80%的人以后不用怎么工作了。人工智能必定会帮助我们解放很多时间,那么我们剩下的时间会做什么?可以自我充实、自我完善等,那时候,人文科学也许会迎来一个更好的发展机遇。
曾湘泉:我认为,中国大学未来还是面临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与经济、社会,包括刚才讲的人口的变化密切有关。我觉得人文学科对于学生打基础很重要,经典的书还是要多读,也要更强调基础和能力的培养,所谓根深才能叶茂。
学生也需要对自己有一个好的学业和职业规划。未来中国的人才战略,应该是行行出状元,人人都能成才的思路,而不是人人一定要上大学,或者都要上研究生。
调查发现,很多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有限,招人只看985、211,甚至要求地域、身高,这些要求跟工作绩效和工作能力没有关系,对提升人力资源利用效率是无意义的。另外,对中国的教育来讲,未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人才培养能不能走在世界的前列,能不能为国家长期的人才发展战略提供支持?
周忠和:李老师认为技术革命、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大学的教育就业会有根本性的影响吗?
李志民:我们往往会高估技术创新在出现的短时间内产生的影响,类似ChatGPT,我觉得现在的热炒是对它的高估。但同时,由于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我们往往又会忽略新技术对今后十几年的长远影响。我觉得新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但是它对大学的影响,我自己觉得大学的一些功能靠机器是替代不了的。
周忠和: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过去注重知识传播,现在更强调知识创造?
李志民:对。这就好比人发明了汽车,使用汽车出行会更快,但人依旧需要学会走路。人们用ChatGPT要提出合理的问题,但提出问题的能力,就是需要自己学习知识、总结知识的过程。任何一个新工艺或者新技术的产生会提高人的生活质量、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但是我不认为它对人的职业本身会产生很大的冲击。
周忠和:但是它对大学的教育方式和模式可能会发生改变?
李志民:会发生一些改变,可能大学的其中某些功能会在一定程度被取代,比如知识传播的功能。但我觉得对于职业的影响,没有必要恐惧。就业结构会调整,有的职业消失,也会产生新的职业。上个世纪30年代,拖拉机和收割机发明的时候,美国从事农业生产大概有3000万农民。五六十年后,美国直接与农业生产相关不到300万人,这几十年来,职业结构发生变化,有些人成为老师、律师、医生。所以,我觉得新技术对职业结构可能会有改变,但不需要过度担心就业问题。
周忠和: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社会能不能创造一种更宽容的环境,更多样的体系去衡量毕业生?我们政府或者用人单位还应该做到哪些改变?
陈平原:现在的“双非”“二本”的学生出来找工作,连参加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即使政府不允许这么来做,但各单位还是会这么考虑。过去像我的同事中不少人第一学历并不好,可是后来发展得很好。而现在我们假定了第一学历不好,以后很难得到好的发展。
周忠和:实际上这可以从政策管理方面做些工作,即给大家更多选择的机会,而不是学历出生论,否则只会导致更多的内卷和压力。
李志民:我们怎么改变这种评价体系很重要。就像我们讲破"四唯"、破"五唯",为什么这么难呢?因为需要相关主管部门先改,说是破除帽子、不唯论文、破除奖励,但各个部门帽子照发、奖励照评,所以不从根上解决这些问题,改变评价体系就很难。
周忠和:这需要一种系统的设计。
曾湘泉:社会观念也需要改进。劳动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统计性歧视”,即将群体特征强加到个人身上的一种观念或行为。统计性歧视来自用人单位为降低成本而采取的一种招聘策略。单位招聘或甄选需要增加投入,而利用求职者所属群体的一般性信息来推测个人情况,则能节省自身投入。
比如,平均来说,985或211院校较之普通院校学生的综合素质要高,而由于用人单位对单个应聘者的实际生产率做出完全预测成本太高,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利用985或211院校学生素质较高这一群体总体特征,来对每位应聘者个体做出是否给予面试机会的决策。在此情况下,用人单位的确降低了招聘成本,但对优秀的应聘者带来了就业市场不公平问题。比如,马云是杭州师范大学毕业,马化腾是深圳大学毕业,他们并非985和211大学的毕业生。
所以“统计性歧视”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拿群体特征找一个平均数,而要看具体的人。比如,美国常青藤大学招生,SAT考满分也不一定会招,通常会涉及其它许多评价指标。比如,面试很重要。一个教授面试一个学生要花费1-3个小时,还要写面试报告。通常我们没有面试,即使有的话,一个人也就花几分钟。所以,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评价观念和态度,还需要在全社会普及。
我们的立法和司法也要去推进。国外是有反歧视法律的,我们《就业促进法》也有公平就业这一章,但问题是如何落实,仍然没有很好解决。政府应该带头,比如招公务员要硕士、博士,可以这么要求,但是这个职位跟学历的关系是什么,要讲出道理来。这其中很重要的是,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刚才讲到破“四唯”,为什么搞“四唯”,因为没有科学的评价方法,所以人力资源管理需要科学化、专业化、职业化,这样才能识别出人才。


 李真顺
李真顺 贺克斌
贺克斌 梅生伟
梅生伟 周远祥
周远祥 赵华林
赵华林 曾毓群
曾毓群 朱共山
朱共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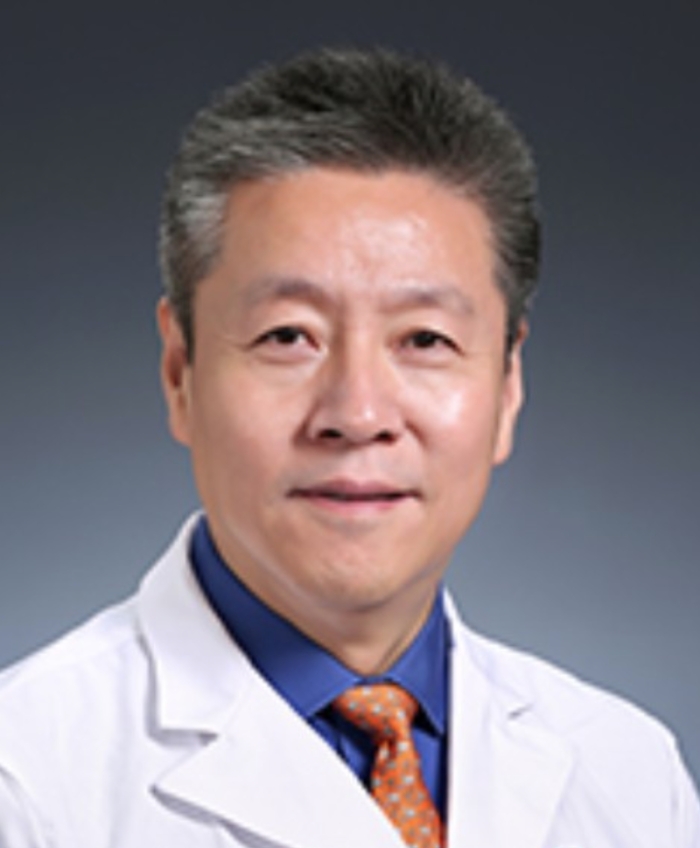 王国玮
王国玮 毛宗强
毛宗强